.jpg) 在1985年秋天,我為開拓台灣養殖的市場而前往到美國。翌年1986年5月,在洛杉磯登記設立營業所,並且訂定初期的營業目標,在和日本的「紅花」公司的青木先生商談鐵板燒使用的草蝦生意時,在台灣東部的火燒島(綠島)監禁中的施明德先生,在獄中進行絕食抗議,震撼了國內外台灣民主及獨立運動的陣營。
在1985年秋天,我為開拓台灣養殖的市場而前往到美國。翌年1986年5月,在洛杉磯登記設立營業所,並且訂定初期的營業目標,在和日本的「紅花」公司的青木先生商談鐵板燒使用的草蝦生意時,在台灣東部的火燒島(綠島)監禁中的施明德先生,在獄中進行絕食抗議,震撼了國內外台灣民主及獨立運動的陣營。▼許昭榮在美國因與愛琳達聲援施明德
而被吊銷護照,成為國際政治難民。
.jpg)
住在南加州的台灣人團體組織到國民政府設立於洛杉磯的「北美事務協調處」門前抗議,展開支持施明德絕食抗議的遊行。
從前就和施家三兄弟有「難友」交誼的我,在面對人情義理的時候,我是毅然決然的參加遊行隊伍,我們大聲高喊「釋放施明德」、「釋放政治犯」、「恢復憲法行政」。熟知,因此不測之災降臨到我的頭上。
淪為「國際難民」
1986年7月14日,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透過駐洛杉磯的外務機關「駐美臺北事務協調處洛杉磯辦事處」,將我的「中華民國護照」回台加簽取消了。
▼在美國期間盟資生堂齊藤雄一先生救助,隱居在日裔坂井圫瑪
斯先生的貿易公司後面的空屋。
.jpg) 因為商務關係進入美國的我,在商務告一段落,原計劃經由日本回到台灣,但因護照的有效期限,未滿六個月,必須到國民政府駐洛杉磯的駐外機關去申請「有效期限延長」手續。這才知道,和亡命到美國的許信良(前桃園縣長前民進黨主席)一樣,我已被列入限制入境黑名單。
因為商務關係進入美國的我,在商務告一段落,原計劃經由日本回到台灣,但因護照的有效期限,未滿六個月,必須到國民政府駐洛杉磯的駐外機關去申請「有效期限延長」手續。這才知道,和亡命到美國的許信良(前桃園縣長前民進黨主席)一樣,我已被列入限制入境黑名單。我唯一在國外賴以證明身分的護照被吊銷後,一夜之間淪為「無國籍者」,想回台灣不能,想居留美國又不得,變成走投無門的「國際難民」,差一點,露宿洛杉磯的街頭!
日本友人的救援之手
在美國本土沒有親友能夠長期庇護我「違法居留」,假如在夏威夷的話,還有情同手足的佐久間先生(日裔第二代)。但即使是如此,能否明知違反美國的聯邦政府的法律敢庇護我,則沒有把握。
很幸運的,經由日本資生堂化妝品公司的齊藤雄一先生的介紹,認識了住在聖塔莫尼卡的日裔第一代坂井托瑪斯先生,讓我住在他商店後面的空屋,使我免於露宿洛杉磯街頭和那些無家可歸的人混在一起。這位坂井先生甘冒違反「美國移民法」之罪而庇護我,讓我「違法居留」。
坂井先生是出生於日本和歌山縣,其義舉使我永遠難忘。他比我大12歲,是一位個子矮小的好爺爺。他動作很快,一點也不輸給年輕小夥子。這就是日裔一世傳統的移民開拓者精神的證據。
他在16歲時,跟他叔父移民到巴西,和出生於阿根廷的日裔第二代瑪莉小姐結婚,在年輕時就已經移居到洛杉磯,他對日本資生堂公司的美國市場開拓,以及商品(化妝品)的推廣有很大的貢獻。因此當資生堂的化妝品的銷售網全部納入百貨公司專櫃經營以後,總公司以「特別恩典」讓他繼續個別經營。
當我陷於「國際難民」之窘境時,台灣還處於戒嚴時期,「白色恐怖」氣氛瀰漫在台灣各個角落,穿便服的「特務」像糞蛆一樣到處蠕動,台灣社會依然處於一種「隔牆有耳」的時代。從女兒寄來的信中暗示我,台灣的特務機關(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及調查局)對我的親戚及公司的同事進行訊問,對我在海外的行動以及言論都掌握在手中。
因為這次的意外災難,使我在台灣的貿易事業,以及美國的商務活動都全面陷入停頓狀態,為了不讓台灣的親友受到困擾,我不得已將一切和台灣的聯絡都斷絕了。
我在美國遭遇到這種不測之災的消息,很快地傳到日本友人及有交易往來的公司,大家都對我的安全非常擔心,特別是日本岡山縣的「遠藤青汁」公司的田邊芳昭社長,他把預定到新加坡的社員慰勞旅行,緊急改為到美西的洛杉磯,趕來探望、慰問,並且支援我一萬元美金的生活費用。
山口縣的千寶貿易公司的藤津社長也特別騰出海外視察旅行的行程來探視,並且親自帶我到洛杉磯的日本總領事館拜訪,打聽政治流亡日本的可行性,並在回日本後,幫我申請東京國際學院的入學許可證,還準備了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的公民證,從各方面協助我。他是和我在日本海軍時的同年兵,戰後,因為商務關係而認識,才成為如自己骨肉一樣的手足之情。
另外丸信公司的有田社長,則透過山口縣選出的國會議員,以及地方上的人脈關係,想救我回日本而不遺餘力。
資生堂化妝品的齊藤先生因為擔心我長期居留生活發生問題,把東京的台和合成樹脂食器公司的美國國內輸入販賣代理權的斡旋,以至打契約都為我安排,而且台和公司雖是初認識,卻以樣品的方式,把各種各類的樹脂食器用20呎長的貨櫃滿載一櫃,完全是以救濟的目的,免費贈送我。
此外,神戶的堀尾社長及廣島的福神製醋公司的佐佐木社長等都非常的關心,真是感激萬分。
▼許昭榮先生榮獲全美台灣人權協會頒發2003年度「鄭南榕紀念獎」赴美授獎時專程到洛杉磯
聖達莫尼卡介護醫院拜望昔日救助恩人,Mr.Sakai(坂井先生)。
.jpg) 在大阪的尾崎產業的尾崎會長,知道我政治流亡加拿大後,在我滯留多倫多期間,每年都寄給我美麗的月曆,讓我紓解思鄉之愁,還有其他商務關係的友人也都非常關心我,真是太勞煩他們了。
在大阪的尾崎產業的尾崎會長,知道我政治流亡加拿大後,在我滯留多倫多期間,每年都寄給我美麗的月曆,讓我紓解思鄉之愁,還有其他商務關係的友人也都非常關心我,真是太勞煩他們了。在長達8年的流亡命生涯中,這樣多的日本商業關係同事以及友人,舊日本海軍的長官、前輩,很溫馨的保護我,才能讓我安全的度過這些歲月,實在是感激不盡,再次在這裡向這些日本友人致上最高的敬意。
突然來造訪的FBI
這樣很小心的藏匿在坂井先生店後裡的空屋時,有一天突然有二位FBI(聯邦調查局)的女性調查員來查訪我,起先我以為是家庭訪問的女性,當她們提示證件在我面前時才嚇了一跳,我抑住了心臟的鼓動,冷靜的和她們應對。
二位都是20出頭的年輕碧眼的女性,看起來很有氣質並且很客氣,大概有一小時的會談,內容是問我來美國的動機及目的,以及對國共兩方的看法、我個人過去經歷以及我對美國的印象等,最後卻問我「有什麼困難的事情嗎?」讓我吃了一驚。
本來想向她們求救,但是向FBI要求幫助,不就等於是把自己的「秘密」向敵洩露一樣,假如沒有求救成功,卻反而發生反效果,那不更糟糕,因此就沒有說出口。
「現在是沒有什麼困難,將來假使有發生困難時還請多多幫忙」,我為了有萬一時還是這樣的表示一下。
「一定的,會幫你忙的」,我得到了很好的回應。
「可不可以請你給我一張名片好嗎?」
「哦!我們並沒有準備名片。」這樣的回答後,其中一位用便條寫了名字及聯絡電話給我。
把二位年輕的女調查員送出門外後,我的胸中像放下一塊石頭一樣。
政治流亡到加拿大
在FBI來訪之後,我的心中漸漸產生了危機感,我去函想借重流亡華盛頓特區的台灣大學國際法學博士彭明敏教授的智慧,彭教授回函,認為美國的雷根政府和台灣的蔣經國政權在私底下有秘密交流關係存在,雖不會加害,但是接受政治庇護的可能性很低,反而「加拿大」這個國家富有「人道主義」,不如向加拿大政府請求「政治庇護」更為上策?他這樣指點我的迷津。
「好,就去加拿大」,我下定了決心。
我秘密地從台灣把申請政治庇護所必要的證件,諸如受過政治迫害的證據、資料等寄過來。其中有終戰後,因為曾當過日本海軍,而被來台灣接收的蔣介石軍隊盯住,在1947年7月(228事件發生後不久),被國民政府軍脅迫投軍到青島的證據,以及在1955年間,廖文毅先生等人在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時,發行的「台灣獨立運動十週年─1955」為題的宣傳小冊,因我不經意的從美國帶回台灣,而因此被判十年徒刑送到「火燒島」的證據,在火燒島服刑滿十年後,卻又繼續被「禁足」八年的證據,一併都寄到美國。同時再加上陷身於「無國籍者」的身份,這些證據已經很充足了。我也開始有了信心,全力計畫流亡到加拿大的多倫多。把政治流亡有關係的證件全部請住在南加州的台灣同鄉會理事郭清江先生及林心智先生翻譯成英文。
▼許昭榮正式取得加拿大政治庇護
.jpg) 出發時間,特意選在農曆8月15日的晚上,這是源於中國的傳說「嫦娥奔月」,而把這個日子設定為我的「拂曉的逃亡」(為自由而流亡之日)的時刻。
出發時間,特意選在農曆8月15日的晚上,這是源於中國的傳說「嫦娥奔月」,而把這個日子設定為我的「拂曉的逃亡」(為自由而流亡之日)的時刻。1986年10月(農曆8月15日夜),高掛在洛杉磯夜空的月亮,看起來比台灣更大更亮。在深夜的12時(農曆8月16日零時),我和長期照顧我的坂井先生夫妻告別,坐上用125塊美金買來的中古別克廂型車,靠著一張地圖,頭上頂著又圓又大的月亮,向加拿大的多倫多出發。
▼流亡海外期間與友人合影
.jpg) 總共6天5夜的孤獨旅行,平均一天要跑一千公里的強行軍,大聲的唱著戰時的日本軍歌〈愛馬進行曲〉及〈露營之歌〉,為自己鼓舞精神,而在這幾近破爛車橫渡廣漠的美國大陸途中,我好幾次擦拭了感傷之淚,尤其是當唱到「出了鄉關幾個月,和這頭相生死的馬…馬呀!你睡得好嗎?明天的戰爭是很激烈的,在像降下彈丸之雨的濁流裡,只有靠你能夠平安度過…」,「這裡離開故國幾百里,越離越遠…」等的歌詞時,我無法抑制流下來的眼淚。
總共6天5夜的孤獨旅行,平均一天要跑一千公里的強行軍,大聲的唱著戰時的日本軍歌〈愛馬進行曲〉及〈露營之歌〉,為自己鼓舞精神,而在這幾近破爛車橫渡廣漠的美國大陸途中,我好幾次擦拭了感傷之淚,尤其是當唱到「出了鄉關幾個月,和這頭相生死的馬…馬呀!你睡得好嗎?明天的戰爭是很激烈的,在像降下彈丸之雨的濁流裡,只有靠你能夠平安度過…」,「這裡離開故國幾百里,越離越遠…」等的歌詞時,我無法抑制流下來的眼淚。這個時候,我想起以前經常去觀賞的美國西部電影,想像銀幕上那些坐在搖晃晃的蓬馬車上,盲目地向西再向西前進的女性和小孩們的身影;想像冒著荒天烈日,沿途還得冒著剽悍的印地安人或惡徒們的攻擊……,腦海裡像走馬燈似的,浮現舉家四進未知之地拓荒的安格魯撒克遜民族之勇氣和開拓精神,藉以自我勉勵,隨時喚起消沈的精神,把老爺車當做「愛馬」相依為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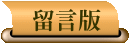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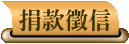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