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不必捨命,連血、汗、眼淚都不必付出,凡不付出任何代價而能得到自由的人,對真正自由的可貴以及感激是無法理解的,這樣的說法並不過言。我親身體會到這個真諦了。
為了「投奔自由」,我從洛杉磯出發,根據地圖,經過拉斯維加斯、盬湖城、丹佛、堪薩斯、奧克拉荷馬、芝加哥、印第安那州、密西根州、賓夕凡尼亞州以及紐約州的水牛城,而來到尼加拉瀑布,費了5夜6天的時間,終於看到嚮往的加拿大。
但是,要進入多倫多的時間,竟然花費了一個多月!加拿大移民局依「違反移民法」罪嫌,把我移送水牛城的「美國移民局」,同時,告訴我:「12月2日上午10時,要到加拿大移民法庭報到受審」。
承蒙水牛城周敦人博士及多倫多林哲夫博士之關懷與協助,美國移民局讓我交保,不限制住所,在美國等候12月2日赴加拿大應審。在美國候審期間,渥蒙水牛城周敦人博士夫婦的照顧;在紐約承蒙羅福全博士夫人毛清芬女士、許瑞峰博士的關照;在華盛頓DC荷蒙李界木博士、蔡正雄博士的照顧,同時,獲得國際特赦組織(AI)、聯合國難民總署華盛頓辦事處、索拉茲國會辦事處、以及多倫多台灣同鄉會、多倫多聯合教會等組織,及林哲夫博士、李憲榮博士、施明雄先生等許多貴人及熱心人士支援下,加拿大移民法庭,很順暢地接納我的「政治難民庇護」的申請。謹藉本書再版之機會,再度向上述協助我、支持我、乃至救援我的團體及個人,致最高的敬意和謝忱。
.jpg) 加拿大的移民法規定:難民縱然獲得居留許可,但未獲「工作許可證」之前還是不能從事工作。但是此時政府會負擔每個月的生活費用及醫療費,實在是名副其實的「人道主義國家」。對這個簽署「世界人權宣言」的國家,的確對世界人類沒有羞辱國格,這是加拿大給我的第一個印象。
加拿大的移民法規定:難民縱然獲得居留許可,但未獲「工作許可證」之前還是不能從事工作。但是此時政府會負擔每個月的生活費用及醫療費,實在是名副其實的「人道主義國家」。對這個簽署「世界人權宣言」的國家,的確對世界人類沒有羞辱國格,這是加拿大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加拿大政府及人民的溫馨重義
把加拿大和台灣讓我來比較的話,那真是有如天堂與地獄之差。台灣是我出生的故鄉,而且我以國民的身份克盡服兵役及納稅的義務,但是台灣的政府不但沒有對我的生活上有任何幫助,甚至連生存的權利都要剝奪;連最基本的人權都被剝削。
另方面,加拿大對我來說,不只是人種、風俗習慣、以及語言都不同,而且從未繳過稅金,也沒有服過兵役,我對加拿大這個國家及社會根本沒有一點貢獻,這個毫無相干的政府卻對我從個人生活、健康保險,甚至生命安全的保護全部照顧,同樣出生於人類社會,為什麼會有這樣像雲泥之別的人間價值呢?當我流亡加拿大,才發覺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而痛心不已。
▼許昭榮與林哲夫(左)合影
.jpg) 多倫多聯合教會設有針對來自各國的難民做短期間收留的設施。我馬上被安置在這裡的宿舍。那天晚上,我到底是應該高興,還是悲哀,胸中充滿著悔恨與驚喜。設施是男女分開,但另外有家族用的房間。我們的餐食是由同樣接受政治庇護的衣索比亞及伊朗的女性來負責。到了12月22日,耶誕節在即,教會要把我們這些難民分配寄宿在職員們的家裡,讓我們能和他們的家族一起度過耶誕節新年。當我向他們申請希望和住在加拿大的台灣人共度新年時,政府答應負擔房租和生活費用,每半個月支付480元美金,這樣持續了一年,其他如健康保險也周到的照顧,這在台灣是絕對無法想像得到的福利,我真是對加拿大政府及國民深深地感激。
多倫多聯合教會設有針對來自各國的難民做短期間收留的設施。我馬上被安置在這裡的宿舍。那天晚上,我到底是應該高興,還是悲哀,胸中充滿著悔恨與驚喜。設施是男女分開,但另外有家族用的房間。我們的餐食是由同樣接受政治庇護的衣索比亞及伊朗的女性來負責。到了12月22日,耶誕節在即,教會要把我們這些難民分配寄宿在職員們的家裡,讓我們能和他們的家族一起度過耶誕節新年。當我向他們申請希望和住在加拿大的台灣人共度新年時,政府答應負擔房租和生活費用,每半個月支付480元美金,這樣持續了一年,其他如健康保險也周到的照顧,這在台灣是絕對無法想像得到的福利,我真是對加拿大政府及國民深深地感激。因為他們不但庇護我的生命安全,甚至保障我最起碼的日常生活,長達一年。
日本政府及官員的冷酷無情
在太平洋戰爭中,特別是在日本海軍海兵團受訓的期間,我們被教育把英、美國人,叫做「英美鬼畜」。到了戰後,當我遇到這次意外之災、淪為難民而流亡到加拿大,實際上和白種人有了接觸後,我才感受到他們的人情味,才明白以前日本所告訴我們的所謂「鬼畜」,完全是不一樣的污衊,讓我對英國人及美國人的印象做了新的修正;這次在北美遭遇災難,陷於進退兩難困境時,卻被以前所敵視的白人政府及人民所拯救乙事,和現營地的日本大使館,或總領事館的官僚們相比,我對白人們的溫馨,銘感肺腑。
當我淪為國際難民時,我首先閃入腦海裡的求救對象,就是駐洛杉磯的日本國總領事館,當然這有它的理由,我會被迫入今日困境的根本原因,因為我是在日本政府統治下的台灣出生,接受日本的義務教育,在戰爭中,我以日本兵身份為日本而戰,就是因為如此,戰後被來台灣的國民政府所鄙視、所嫌棄,接著被政治迫害而陷「無國籍國際難民」之身。從常理來講,我第一個求救的目標,當然是日本政府。連日本的友人及商務關係的人們,都對我的不幸遭遇擔心,伸出援手,何況是代表日本國的大使館或領事館的官員們,更不應該沉默不理。於是我很天真的跟專程從日本山口縣飛來美國的友人藤津宏之助先生去拜訪駐洛杉磯的日本國總領事館的首席領事中村義博先生。但是日本政府,到現在卻連「政治庇護」的名詞都沒有,甚至連對「國際難民」的救援措施都還沒有制定,所以中村領事的結論是「以個人來說,我是無限的同情;但是以國家或政府來講,現在連救助的方法都沒有。」這種外交辭令實在令人灰心。
「實在沒辦法」,藤津先生只好頷首承認了,但我的心中卻因失望與悲憤而疼痛不已。
所幸的是,先前提到的AI及UNHCR等組織以及華盛頓特區的索拉茲參議員事務所、駐華盛頓的加拿大大使館、多倫多台灣同鄉會等等,對我伸出了熱誠的援手。
在華盛頓特區滯留中,我經由聯合國難民總署的介紹去拜訪加拿大駐美大使館,探詢在12月2日進入加拿大的可能性。這時。有位碧眼銀髮的中年女性職員很親切的輸入電腦確認後,帶著笑容地對我說:「一切沒問題」。
走出加拿大大使館的正門後,我真是感慨萬千,為了給在水門的日本國駐美國大使館一點找麻煩的臉色看,我專程走訪日本大使館那裡,坐在視窗負責接待的女性職員用很冷淡的臉迎向我,而坐在中間的30歲左右的男性館員也用官僚的眼神向我瞥。
「我是遠自洛杉磯前來探詢的原日本兵台灣人,叫做許昭榮。因為有事,向貴國駐美大使請願,能否給我方便和他見面?」我說明瞭來意。
「大使有事外出中。」
「什麼時候會回來?」
「不曉得,有什麼事?」
我心裡想:對接待的女性館員說也沒什麼用,於是拿出事先準備寫好的「中曾根總理大臣親展」的大信封交給她。
「喲,這是什麼?」
「這是政治庇護請願書啊!」
這時候,看起來很傲慢而靜靜聽我們講話的男性館員站起來,走到櫃檯,不在意的看著信封,終於開口了。
「我們不能接受這種東西。」
「那麼大使不在的話,總領事應該在吧。跟你們講也沒有用,我要見總領事」,我開始沉不住氣大聲說。
這樣一來一往以後,總算讓我和一等書記官的加藤邦夫先生見了面。
加藤先生足足2小時很沉住氣的,聽完我充滿不平的控訴,我也很不客氣的把日本官僚的「冷酷無情」的態度以及「經濟動物」的氣質,直接了當的批評。
「我是一個國家公務員,老實說,對於和日本沒有邦交的台灣人民的苦情,我是沒有聽取的必要,但是以個人來說,對於你陷入苦境,是有非常同情。但是因為這是國家的規定,實在很抱歉,我們是無法幫忙的。」加藤一等書記官也紅了眼眶。
「很抱歉,打擾你,其實我已經決定向加拿大提出政治庇護,你也不必太過意不去,只是中曾根總理大臣在戰爭時曾經在高雄待過,這些書類希望能轉交給他,給他做個參考。」我把「政治庇護嘆願書」親手交給加藤一等書記官。
「到加拿大的什麼地方?」,加藤先生羞慚地紅著臉,放下心似的說。
「多倫多」
「那麼我給你介紹多倫多領事館的藤原稔由領事好嗎?是我的同級生,有什麼困難時,請跟他聯繫?」加藤先生給了我藤原領事的電話號碼後,很親切的送我到樓下的門口。
在多倫多定居下來後,我為了對加藤一等書記官答謝,打過了電話,那時他卻已經榮調到印度的孟買去了。
多倫多領事館的藤原領事已經從加藤先生聽到我個人的事,因此當我去造訪時,他很大方的請我吃了16盎司的大牛排。但是當我在1989年2月,拿著加拿大政府發給的「難民護照」要去中國大陸尋找戰友的遺骨,而申請過境日本,要和岡山市的田邊社長會合一起去北京,去申請日本入國簽證時,住多倫多的日本國領事館卻依然駁回對我的申請。當時,藤原領事仍以「國家公務員」的立場,一點也不通融。我對戰後日本的變化確實感到訝異。以前教育敕語以及大和精神就像做夢一般,像說謊一樣消失了。況且派駐北美的日本外交官應該都是日本外務省所精選的優秀外交官,然而在我眼中所出現的竟是不但沒有大和魂,更沒有人情味,更像一部機器人。
因此我曾經想把這本書的名字定稱為《啊!無情的日本官僚》。在日本人裡面有很多比我自己台灣同胞更愛護我的人,但為何這些日本國的「政客」、或是日本政府的公務員對處理戰後「原日本軍人軍屬台灣兵」的態度竟是那麼冷酷無情,我實在是無法吞下這口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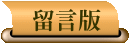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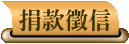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