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共軍俘虜,而殘留在中國大陸四十幾年的原日本軍、原國民政府軍台灣老兵們所遇到的最大災難是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大約有90%的台灣老兵被以「歷史反革命分子」、「日本軍閥殘餘分子」、「國民黨特務」、「台灣間諜」、「黑五類」等嫌疑而遭到逮捕,他們一再地接受苛酷的審問,被認為重罪者關入監獄,或者送到偏遠的邊境地區的集體農場或礦區進行「勞動改造」。罪較輕者,則被戴上三角長帽,頸上掛著「歷史反革命分子」、「日本軍閥殘餘分子」、「黑五類」等用大黑字寫的木牌吊在胸前,被帶到街上去遊行示眾;有更甚者,被拉出去交給「批鬥大會」,被群眾拳打腳踢,被眾人吐口水在臉上,遭受身心俱破碎的無情打擊。因此在文革期間,滯留在中國的台灣人都是隱藏自己的身份,連一個台灣的「台」字都不敢說出口,甚至連台灣人之間的互通音訊都斷絕了。
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被送到黑龍江省與西伯利亞國境附近的「紅星農場」勞改的原日本軍、原國民政府軍、原人民解放軍的重機關槍射擊兵陳力芬先生(台灣基隆市人),對每日加在身心上的侮辱無法忍受而跳入農場的水井自殺,他是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出生,接受日本的精神教育,在二次世界大戰時被日本軍徵為「榮譽軍夫」,派赴到中國大陸去當通譯,而後來因體格壯碩被編入重機關槍分隊而被派到前線。
在激烈戰火中得以倖存的他,對日本的戰敗流下遺憾之淚。復員回到台灣後,第二年,當他看到在基隆登陸的「國民政府軍」的裝備,讓他想起在中國大陸常見的「支那敗殘兵」的那種形象,他大為感嘆。
「日本怎麼會敗給這種敗殘兵?」他後悔的忍吞下眼淚,到了傍晚,他常徘徊在基隆的港邊,想找尋密航到日本的機會,不久發生了「228事件」,事件的火焰立即擴及到台灣全島。
陳先生以日本復員兵的身份參加學生隊,擔任指揮。「這些清國奴」面對那些中國兵這樣罵著。為了報復敗戰之仇恨,他很勇敢地衝向中國軍派來的鎮壓部隊,但是非常可惜,「228事件」終於被鎮壓,討伐暴政的國民黨政府之反抗行動失敗了。
於是陳追捕的名字在隨後的「清鄉掃蕩」行動中成為被追捕的對象,他終於被逮捕了。當時的國民政府隊是極度的橫暴,人民發生糾紛,動輒把槍口對準你的面前,大喊「槍斃!槍斃!」簡直目中無人的狂態。陳先生沒被槍斃,但是憲兵隊長清查了他過去的經歷,僥倖發現他是從中國戰線復員歸來的原日本軍,因此認為與其報復,不如利用他的存在價值,把他移送陸軍,這樣他就被編入第七十師,三八四旅第三連隊的重機關槍隊,又把他送回到中國的戰線,這次並不是日本兵,而是國民政府軍的重機關槍士去和中共的八路軍作戰。
被強制變貌為「支那兵」之後,他對中國人的憎惡感越增加,他身在部隊中但心中經常謾罵「糞臭的中國豬!」。
在徐州戰役,他逃過幾次死亡,也幾度計畫從部隊中逃亡,但是被監視的很緊,最後因脫逃失敗而被捕時,他差點要被捉去倒栽活埋,不久國民政府軍吃了敗戰,他也被中共軍俘虜了,他以為戰敗時,可能會撤退到台灣而回家。誰知被俘後馬上被換了帽徽,這次成了「人民解放軍」的兵士,反而要去追擊敗走的國民政府軍。
為了要追擊敗退的國民政府軍殘兵敗將,一直南下到舟山群島,再進擊下為就可能越過台灣海峽回到台灣,正在高興時,卻因爆發了朝鮮戰爭,部隊便急速的被移動到北方,因此他的夢想又再度破滅了。這時,他已經開始覺悟自己,竟有這種惡戲般的命運。
1950年10月,陳力芬又以「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身份渡過鴨綠江,被送到北韓的溫井地方,對付美軍的猛烈砲火,「抗美援朝中國人民志願軍」採用了游擊戰術。
他在激烈戰鬥中,甚至在行軍中,都會突然地在心中叫喊「我到底是真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嗎?」也經常會大聲叫喊起來而嘲笑自己。
陳先生因為在第二次的三十八度線奪還戰役中,胸部及右腳受了重傷,差一點就喪失了生命,他被送回中國,在瀋陽的醫院繼續療養,這期間中共正好開始所謂「三反五反」運動,他在負傷療養回復後,又被送回軍隊。
1966年6月中國共產黨發動「文化大革命」,陳先生此時被紅衛兵拉出來,被扣上「日本軍閥殘餘分子」、「國民政府特務」、「歷史反革命者」的罪名,送到人民公審被灑小便、吐口水再加以拷問,把參加「人民志願軍」的功勞扣抵後,總算是可以免除徒刑,但是被判定放逐到黑龍江省的中蘇邊境的「紅星農場」,他不得不每日非常厭惡地接受思想及勞動改造。但是每天所加上的各種人格上的侮辱,讓他受不了,終於在農場內跳井而自殺。
原日本軍的「榮譽的軍夫」,「原國民政府軍」、「原人民解放軍」、「原中國人民志願軍」的重機關槍士的陳力芬竟這樣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自我「解放」了。當我在哈爾濱聽到這樣的悲慘事件時,我當場掉淚,低頭為陳先生祈禱了冥褔。
我發誓我要把他的遭遇記下來,做為歷史的證言,永遠流傳下去。
「文化大革命」時代,全中國不知有多少台灣人和陳力芬先生一樣遭遇到同樣的命運,真遺憾,到今日為止,不但政府對他們被無情地推入這樣悲慘的境地之事不負責任,連對他們的悲慘命運寄予「憐憫之心」的慈善家也沒有,像這樣沒有責任的政府,以及沒有神經、沒有公義的社會,天上的神明怎麼不聞不問不可思議。
被流放到中蘇邊界的台灣老兵
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1976年)中,滯留在中國大陸的「原日本軍、原國民政府軍」的台灣老兵,幾乎都是成為紅衛兵的鬥爭對象,特別是像陳力芬先生一樣具有「日本精神」的台灣人,都遭受到殘酷的悲慘境遇,被送到中國邊境或是最偏僻的地區流放。單以我手中所收集的移送黑龍江省的人數與名單如下:

原日本軍屬羅登輝的哀歌
曾經是「原日本軍屬」、「前國民政府軍」,接著又成為「人民解放軍兵士」的羅登輝先生,與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先生雖僅一字之差,但是他和陳力芬先生一樣是一個人扮演三種角色,一生中充滿了一波波悲哀的命運所翻弄的人物。
他是1920年出生於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台中州豐原郡,在中華民國(1989年)78年12月25日死於中國江蘇省泗陽縣的異邦之地。
依照中國共產黨的資料所記載,他是「8歲到14歲入學就讀,14歲到21歲當職工,而後當二年日本兵,又當了三年的國民政府軍,在海南島的榆林自營建台營造所(其實是木工店)一年三個月,在1950年8月18日在海南島被解放(俘虜)成為人民解放軍」。
羅登輝先生為了準備在萬一時能留下自己的記錄而在壁中藏了二張記述如下的字條:
「我的名字叫羅登輝,原籍台灣台中州豐原郡,昭和18年(1943年)9月25日,被徵用為日本軍夫,被派遣到海南島,直到終戰為止。而後,被來接收的海南島的國民政府軍所強制留用,到了1949年才辭去軍職,因為自己是木匠,因此一面工作,一面等待著回台灣的船隻,但是在第二年就被中共軍俘虜而被送到中國大陸,過了五年的人民解放軍的軍隊生活,在退役後,又在泗陽縣的埠頭當了五年的貨物搬運工,而後被逮捕,無端被套上歷史反革命罪而判懲役十年,勞動改造二年六個月。」
「在獄中因為生病,雖被允許保外就醫,但卻是被移送到地方的人民公社農場,在群眾的監視下進行勞動改造,到了1973年方總算獲得自由之身回到民間,我現在的願望只有一個,就是能夠回到故鄉的台灣,完成落葉歸根的心願。」
另一張已經發黃的字條記遊如下:
「1943年9月,我被徵用為日本軍夫派遣到海南島。我的任命是配屬於日本橫須賀海軍第四特別陸戰隊的三等巡警(實為戰門員)。月薪是日幣85圓50錢。1944年4月升為三家分遣隊的二等巡警,1945年4月又升為二甲分遣隊一等巡警,直到終戰為止。終戰後,我被來海南島接收的國民政府軍以台灣人技術者留用,在1946年3月強制收編派到三亞市國民政府軍航空基地服務,待遇是陸軍上士(軍曹)。
本來聽說在九月份有開往台灣的船隻,包括我在內的原日本軍人,軍屬、軍夫台灣人共39人都在為返回台灣而準備,但是不幸的是,因為遇到颱風,基地內的兵舍被吹倒了,我們被繼續留下來整建,因此就失去了回台灣的機會。從重慶派來接收的羅司令官告訴我們:『過了新年以後,若有船隻的話,會把舒適的船室留給你們,優先讓你們上船,假如沒有船隻的話,我們才會用空軍的飛機送你們回台灣』,這樣對我們保證,但是新年過了很久,仍然沒有遣送我們回台灣的動靜。後來,我們才知道羅司令官根本是在說謊,那一張蓋上官印的公文,只是一張廢紙一樣,根本沒有作用。
當時三亞空軍基地有一位原叫傅榮華的福建人部隊長,他在1948年時,突然改名字姓「龍」,我是在1949年得到他的許可獲得離開基地的職務,同時為了回台灣,向國民政府的關係機關提出「台灣入境簽證」的申請書,但是到現在為止,連一點回音都沒有,到現在還未能實現回台灣的願望。
國民政府的法令和規定不但亂七八糟,而且馬馬虎虎,官員的作法又是貪汙骯髒,為什麼國民政府軍的台灣兵不能回台灣,真是不可思議。於是不得已,自己開了一間稱為「建台營造所」的木工店,一人孤獨生活,等待回台灣的機會。到了1950年4月,駐在海南島的國民政府軍秘密地撤退到台灣,而我們這些台灣兵卻被留在海南島,到了同年8月,我們便被中共的人民解放軍解放(俘虜)了。」
成為羅登輝先生遺書的這二張字條(便箋),悲痛的告訴我們,在終戰的當時,殘留在海南島的原日本軍人軍屬的台灣人如何地被國民政府軍強制留用,又如何喪失搭乘日本軍的撤退船隻及國民政府軍的撤退船艦的悲慘故事。
他們每天站在長著椰子樹的海南島海邊,忍住眼中的熱淚,眺望著碧海和青空,腦海中浮現所懷念的故鄉的種種回憶,渴望著與久別、等待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團圓。但是,生為「台灣人」的他們,被日本人區別成「支那人」,又被中國人歧視為「日本兵俘虜」,把他們當做「戰利品」,就像皮球一樣,由這一手傳過另一手,不斷地被強迫去參加那賭注生命的「戰爭遊戲」。
依照我的踏查訪問,終戰後在海外被國民政府軍接收而強制留用的台籍原日本軍人軍屬不只是羅登輝等人這種情況,其他尚有國民政府軍第四十六軍第一一八師也有被強制留用的原陸軍野戰醫院的軍醫及護士,還有,不少被國民政府軍的輜重部隊所強制留用的運輸司機。去年終於回到台灣的花蓮縣出身的陳增昌先生(原日本軍醫)及張壬妹女士(原護士)夫婦,早前脫逃回台的徐秀棟先先;現在還留在海南島海口市的宋道昌及鄭潤啟兩先生,也都是原日本軍的原國民政府軍的台灣兵。
到底有多少原日本軍人軍屬於終戰當時,在海南島或中國大陸被國民政府的軍隊所強制留用?而後,他們的境遇又是如何?研究台灣近代史的學者,或是對「原日本軍台灣兵」以及「原國民政府軍台灣兵」有興趣的人權工作者實在有加以探究的餘地及價值。
戰後,已經經過了五十年,但是對「台灣老兵」的苦難和悲劇知道的台灣同胞不到百分之一,這可以知道五十年之間的國民政府的「愚兵愚民政策」以及「殖民教育」是如何根深蒂固地浸透入台灣人民的幼稚心靈,真是可嘆可悲的事。
話說回來,1943年羅登輝被日本軍徵用到南方戰線出征時已經結婚,而他的妻子也已經是妊娠八個月。
利用台灣兵來攻略台灣
1945年8月,日本敗戰後,被派遣到南方戰線而砲火餘生的台灣兵日本軍人軍屬陸續復員回到台灣。羅先生的妻子羅碧玉女士抱著幼子每日等待夫君的歸來,但是羅先生到最後都一直沒出現。
對丈夫被國民黨軍隊強制留用,甚至被國民政府軍棄置而又被中共軍隊所俘虜,再被送到中國大陸的事,在台家屬當然不可能知道,碧玉女士每日忍著淚水撫養幼子,朝晚對著丈夫的牌位燒香泣拜。
成為中國共產黨軍隊俘虜的羅登輝,被編入人民解放軍「台灣幹部訓練團第三中隊」,次年九月,被配屬到「華東直屬集中訓練隊」。但是歷任日本軍的戰地員警,並晉昇到一等巡警的他,在1952年7月,被中共當局評價為「表現不良」降為「炊事兵」。
當時,中國共產黨軍乘勝追擊,想解放台灣。中共當局認為要攻略台灣,可以利用台灣俘虜兵,因此計畫如何對台灣兵洗腦當做攻略台灣的尖兵。
考據中國方面的文獻,從1947到1949年之間,在國共內戰中,被中共軍所捕虜的原國民政府軍台灣兵大約有二千人,他們全部被編入「人民解放軍」,而準備攻略台灣。有一部分被移送到華北或華東的「軍政大學」,接受三個月或九個月的短期促成幹部訓練班,而大部分的台灣兵則被送到各地所設置的台灣幹部訓練團,接受馬克思思想的洗禮,而後集結到浙江省及福建省的沿海基地,一步步地準備著進攻台灣。
沒想到,1950年6月25日,突然爆發了朝鮮戰爭,美國海軍第七艦隊急遽地派遣至台灣海峽介入防衛台灣,就這樣,中共軍的「台灣解放攻擊計畫」變成白紙,避免了一場台灣人殺台灣人的「互殺悲劇」。
羅先生可能是因為在訓練中「成績不良」的關係,不能擔任攻略台灣的尖兵,才被淘汰降為「炊事兵」,被轉派到江蘇軍區訓練團的第四大隊第十二中隊的。到了1955年春天,他又恢復了「戰鬥員」的身份。此時,朝鮮戰爭已經停戰,中共軍又再度集結到南中國海的沿岸,想乘佔據浙江省台州灣的小島「一江山」之優勢,準備進攻金、馬。
什麼是台灣人的「歷史反革命」
離開故鄉台灣十幾年,而且國共雙方對立,連通訊都不可能,還鄉的日子更是遙遙不可期,羅登輝在這環境下終於和江蘇省的女性張秀蘭結婚,第二年生下一個女孩,取「泗陽」的字頭,稱為「泗妹」,夫妻子女三人雖過著苦日子,總是一家團圓生活,但不幸的是他的團圓日子並沒有持續多久。
1960年1月11日過了新年,還不到二個星期,羅登輝因為有「原日本軍」、「原國民政府軍」及「台灣人」的三重身份,以「歷史反革命」份子的罪嫌被逮捕,並被判處徒刑十年、勞動改造二年半。他的妻子也被列上「黑五類的家屬」之名單而遭受到辛酸的生活。
1962年6月,羅先生因為在獄中罹患了肺腫病,雖獲得保外就醫的許可,卻是被移送到泗陽縣人民公社,在群眾監督下進行治療。
從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間,所謂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幾乎所有的滯留在中國大陸的台灣人,包括早期的台灣共產黨領導者謝雪紅、留學日本的知識分子,及殘留中國的原日本軍、原國民政府軍台灣老兵等不論身份,全部被指為「歷史反革命份子」,連大陸籍的妻子都被列為「黑五類家族」過著受迫害的日子。
尤其,特別是像陳力芬、羅登輝兩人一樣受過日本教育而經歷日本軍人軍屬,尚未能完全脫離日本精神的人,更是成為中共紅衛兵的「眼中之刺」遭受到悲慘的待遇。他們的苦難,實在令人同情。
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到底和台灣人又有什麼關係呢?推在台灣人身上烙的所謂「歷史反革命」的罪名到底又是為什麼?是根據什麼法律?到現在我還想大聲的責問「紅衛兵」那些傢伙。
這個「歷史反革命」的罪名,雖然因為鄧小平的上臺而抹消、而平反了,但是每想到中國人對台灣人的「政治迫害史」,簡直像心內在滴血一樣感到悲哀。
在「洞窟」的家迎接新年渡過寒冬
1970年1月10日,羅登輝先生服滿了十年的徒刑獲得釋放,但是脫不了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又繼續被送去勞動改造二年六個月。
歷盡太平洋戰爭以及國共內戰,穿過槍林彈雨,砲火餘生的羅登輝,沒有辯駁的餘地,不得不服從無須有的懲罰。他感嘆:「枉費上蒼保佑我羅登輝存活下來,然而,因為生為台灣人的「原罪」,難道我必須再背負十字架,非死在「勞動改造營」不可嗎?這是什麼道理!」他一想起這些事便悲傷得有幾次想自殺,但是回想留在故鄉的妻子,年紀老邁的雙親,還有未見面的兒子,故鄉台灣的種種縈繞在他的腦中,於是他繼續咬緊牙根。
「為對抗這些畜生我要勇敢的繼續活下去」,他這樣勉勵自己。
▼羅登輝和家人住了17年的土磚茅屋
.jpg) 1973年12月,他被中共當局評定「表現馬馬虎虎」獲釋回復為自由之身,然而卻攜妻帶女走投無路。想回台灣嘛,在國共雙方對立的情況下,回台灣是不可能的,這是不言可喻。更何況,在中國大陸又已經再婚,把妻女帶回台灣必定會發生家庭糾紛。想離開這個使他厭惡的泗陽嘛,沒有「通行證」是走不了的。考慮到最後,任由命運的安排接受了看管運河的堤防的工作。
1973年12月,他被中共當局評定「表現馬馬虎虎」獲釋回復為自由之身,然而卻攜妻帶女走投無路。想回台灣嘛,在國共雙方對立的情況下,回台灣是不可能的,這是不言可喻。更何況,在中國大陸又已經再婚,把妻女帶回台灣必定會發生家庭糾紛。想離開這個使他厭惡的泗陽嘛,沒有「通行證」是走不了的。考慮到最後,任由命運的安排接受了看管運河的堤防的工作。江蘇省的冬天是很冷的,而且風雪又大,對困窮人家而言,更是雪上加霜!羅先生一家三人在新年快要到的這時節,不但沒有錢,連躲避風雪的家都沒有!他們像被秋風掃盡葉子,站在堤岸上震顫的防風林,在寒風中全身顫抖著,祇有望著灰色的天空,向上蒼祈求春天早日來臨。
當年被派遣到海南島,和當地部落居民同樣生活在野外有相當時間的羅先生,為了渡過這樣寒冷的冬雪,在堤防的土堤上挖了洞窟。想不到卻挖到尚未腐朽的棺材和白骨。人一旦窮途末路到了這種地步,什麼鬼神、禁忌都不怕了。他把腐朽的棺材和白骨收集起來,另外挖個洞穴把這些埋回去,然後把原來的墓穴再挖得更寬闊到能容下三個人住得下的程度。
這一年,羅先生一家就靠著政府所配給的少量糧食,在洞穴中迎接了新年,總算渡過了寒冷的冬天。過了年後,開始吹起暖和的春風。他自責讓妻女住在墓穴實在太可憐了,於是挖了河床的泥土做成土塊砌成牆壁,割了河邊的茅草蓋上屋頂,總算建成了大約六坪大小的小屋,三人便住在這個土磚茅屋(如圖)渡過了十七年的歲月。
在此期間,羅先生擔任了運河的堤防及防風林的管理,有空時,利用時間到碼頭去從事貨物搬運工作,而秀蘭和女兒泗妹則一起到市場或菜園去撿拾被丟棄的野菜或農家沒有撿拾的雜穀或蕃薯來補貼生活。
望鄉及羅妻秀蘭之死
到了1987年末,台灣的國民政府被國內外要求「返鄉探親」的聲浪壓迫,終於對中國大陸解除門禁,使敗退到台灣的國民政府軍退伍老兵(外省人)能夠在四十年後返回了他們的故鄉。
但是,另一方面國民政府對滯留在中國的原國民政府軍台灣老兵的歸還問題卻制定了許多不人道的規定,禁制台灣老兵回鄉。致使羅先生變得急躁不安,沒有食慾又失眠,每天到運河的碼頭或街上的停車場徬徨徘徊,一看到好像從台灣回來「探親」的老人,就靠近去請他們幫他帶一封信,寄給台灣家族。他這樣四處尋人拜託。
他曾經肩上掛著紅色佩帶,在日本的太陽旗及榮譽軍夫歌聲歡送下,出門已經過了五十年。在這漫長的五十年歲月裡,羅先生的銳氣以及自尊,已經完全消失了,身心都已經無力,心中所留下來的唯一心願就是能早一日回到台灣的故鄉,但是在此之前,他必須和故鄉的親人取得連絡,因此他的內心是非常焦急的。
自從國民政府軍外省籍老兵開放「返鄉探親」以來,羅先生的鄉愁是日復一日增加,但是他的歸鄉慾念越是強烈,他的妻子秀蘭就反而越是意氣消沈,最後,連雙方的對話都沒有了,終生苦勞又營養不足而一直患貧血症的秀蘭對離開泗陽好像很不願意。
有一天,突然不幸來臨了,和平常一樣在運河畔洗衣服時,秀蘭突然發生腦貧血而掉入運河裡溺死了。這時羅先生仍和往常一樣在街上找尋從台灣回來探親的外省人老兵,他接到惡耗跑回去時,他的妻子已經沒有氣息了。
羅先生自責沒有盡到做丈夫的責任,把妻子的遺體葬在自己小屋的旁邊,以便能每日和妻子相望、對話。秀蘭死後,羅先生的精神負擔稍微減輕了,他和唯一的女兒泗妹過著父女相依的生活,但每日還是燃燒著回歸台灣的願望。但是很遺憾的,他在這個期間裡,還不知道他在海南島出征時,大腹便便的髮妻碧玉,也已經在十幾年前離家再婚了。
羅氏父子初會面的喜悅
1988年夏天,羅先生終於和台灣的親人取得連絡。從來信的筆跡可以確認是羅登輝的親筆信函,但是家人一時無法接受這個事實,他們認為以日本軍夫派遣到海南島而戰死的羅登輝,在四十年後,竟然活生生的在中國大陸,家族們做夢也沒有想到這一點,只是半信半疑,但是同樣的來信從中國不斷地傳來,這時家族對他生存的事實不得不相信,而燃起一絲希望。大家討論的結果,決定組成旅行團藉著觀光到江蘇省泗陽縣去探望。
▼羅登輝(左)和兒子羅鐘雄重逢
.jpg) 雖然羅登輝離家已經45年,但他的妹妹一眼就認出哥哥羅登輝。兄妹闊別了40餘年,悲喜交集;羅鐘雄更感到驚喜,因為這是他出生以來第一次見到自己的父親。父子首次見面,驚喜的擁抱,喜極而泣。一起參加旅行團的人,不論親戚或外人,莫不被這幕親情所感動,情不自禁地跟著落淚。
雖然羅登輝離家已經45年,但他的妹妹一眼就認出哥哥羅登輝。兄妹闊別了40餘年,悲喜交集;羅鐘雄更感到驚喜,因為這是他出生以來第一次見到自己的父親。父子首次見面,驚喜的擁抱,喜極而泣。一起參加旅行團的人,不論親戚或外人,莫不被這幕親情所感動,情不自禁地跟著落淚。尤其,當大家看到羅先生一家三口住了17年的豬舍不如的茅屋,更禁不住同情和關懷之情。要離開泗陽時,一道參加旅遊的同伴,大家都把多餘的錢,(包括美金及人民幣),全部掏出來交給羅登輝。
堂兄羅團長代表參加旅行的團員,對羅登輝說:「用這些錢去蓋一間鋼筋水泥的覆瓦二層樓房吧!如果不夠,請告訴我」加以叮嚀後,緊緊地握住了羅登輝的手。
破滅的歸鄉之夢
父子見面後的一個多月後,羅先生的兒子鐘雄又再度飛往泗陽,這次的最大目的是要去辦理父親返台所需要的手續,中國政府方面已經發給返鄉羅登輝的回台許可書。羅先生用拐杖支柱七十二歲的身軀和兒子一起到設置在香港的國民政府簽證辦理機關「港九救濟委員會」去申請回台的「入境簽證」,但是在九龍的金門飯店住了三個月,幾乎把所有的旅費都用光了,台灣方面的入國簽證卻一點消息也沒有,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最後去拜託有關的人去查詢,才知道台灣的國民政府規定「殘留中國的原國民政府軍的台灣兵」歸台條件「必須年齡七十五歲才能發給入國簽證」。
羅先生父子真是愕呆了,拉著滿臉流下了悲憤的淚,父子二人頓時掉入失望的深淵,只好又回到泗陽自為「豬稠」的舊巢。
從此以後,羅先生每日過著悲憤與憂鬱的日子,結果連出外都變得毫無興趣。
「至少也讓女兒先回去台灣」,這樣子想的羅先生給在台灣的兒子寫了信要他幫妹妹辦理台灣的入境手續,但是所得到的答覆是「隨親回台的子女只限於未滿十二歲」規定的這種惡辣的消息。
當時羅先生未滿72歲,而女兒羅泗妹已滿21歲,父女兩人都沒有回台灣的資格,對羅先生來講,從沒有受到這麼大的精神打擊,感到疲憊的他,禁不住說:「國民政府的法令和規定不但亂七八糟,並且敷衍了事,官吏的行為更是骯髒」,想起以前他對國民政府所批評的話又再一度的得到驗證。確實就是如此,他再度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啃囓他的心!
「好吧!下定決心把鐵筋水泥的蓋瓦二層樓建起來吧!」他心中這樣的發誓。
原日本軍、原國民政府軍台灣老兵的哀歌
靠著台灣的兒子鐘雄的經濟援助及羅先生本人的苦心努力,二層樓的基礎工事終於完成,並且上樑,漸漸地把一樓的水泥壁也完成了,當二樓的屋頂完成時,紅瓦由南京用小帆船載了過來。他是每天日夜的疲勞及悲憤填胸,他肺部的舊疾再次復發他終於倒下來了。
▼羅登輝的兒子幫父親完成的二層樓房
.jpg) 那年(1989),過了八月,進入秋風吹拂,堤防的防風林開始落葉時分,他新建的「鐵筋水泥的紅瓦二層房屋」終於完成了,是這個村裡頗具氣派的樓房。
那年(1989),過了八月,進入秋風吹拂,堤防的防風林開始落葉時分,他新建的「鐵筋水泥的紅瓦二層房屋」終於完成了,是這個村裡頗具氣派的樓房。落成那天晚上,在新屋的庭院舉行慶祝宴席,把村內的男女老幼都請來,其中,連在「文化大革命」時代批鬥嘲笑羅登輝,在他臉上吐口水、用腳踢他的「紅衛兵」也混在裡頭,村裡的官員也來慶賀致詞。
羅登輝抱病由兒子及女兒扶著雙臂,用拐杖拖著老瘦的身軀來到會場,看見好像村子裡大拜拜一樣的熱鬧及喧嚷不息的歡聲,心裡感慨萬千。
「羅先生,恭喜恭喜」之聲不絕於耳。
「羅先生,乾杯、乾杯」這樣被奉承著,但是羅先生卻是笑不出來,連喝酒的興致都沒有,反而是在內心裡哭泣。
專程從台灣趕來參加落成儀式的鐘雄,把父親的台灣「入境許可證」帶來了,但是這時的羅先生已經連出門去旅行的氣力都沒有,甚至連回台灣的意願也沒有了。
就在同一年12月25日,他的「落葉歸根」的悲願就像毫無止境的夢境一樣消失了,他的兩眼含著遺恨之淚,安靜的去世了。
▼新屋落成,羅登輝接受村民的祝賀。
.jpg) 羅登輝先生的人生經過了激烈的太平洋戰爭的砲火、國共內戰悲慘的人海戰術,以及橫暴的文化大革命的屠殺,踏破這些大動亂時代的波瀾而能生存下來,竟然在國共對立緩和,國民政府的戒嚴令廢止,以及兩岸的門禁開放,正要達成歸返故鄉台灣的心願之前夕,卻在標榜民主主義的國民政府的非人道政策對待下氣死!
羅登輝先生的人生經過了激烈的太平洋戰爭的砲火、國共內戰悲慘的人海戰術,以及橫暴的文化大革命的屠殺,踏破這些大動亂時代的波瀾而能生存下來,竟然在國共對立緩和,國民政府的戒嚴令廢止,以及兩岸的門禁開放,正要達成歸返故鄉台灣的心願之前夕,卻在標榜民主主義的國民政府的非人道政策對待下氣死!羅先生的處境就像在戰場上負了重傷,奮力忍受終於回到自己城門下時,卻因為主帥下令不給他打開城門,終於流血過多,死在自己的城門前的武士一樣悲慘。
▼羅登輝的喪禮,落葉歸根的悲願也消失了。
.jpg) 羅登輝先生之死,不只顯示了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同樣也是一種對中國國民黨政權殘暴與不人道的「戰後處理」無言的抗議。
羅登輝先生之死,不只顯示了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同樣也是一種對中國國民黨政權殘暴與不人道的「戰後處理」無言的抗議。和羅先生一樣受到國民政府的這種毒辣的差別政策所打擊而吞下悲恨之淚,失去生命的殘留在中國的原日本軍、原國民政府軍到底有多少人呢?這樣殘酷的史實,被國民政府的忽視而將漸漸消失在這個二十一世紀的「自由民主與科技的時代」裡。我無法容忍這種悲傷而讓它迢遙流逝。只要我意識存在的一日。我絕不氣餒,雖然是詞不達意的文章,我要趁早把這個史實寫下來,也要把它出版,讓大家知道這段史實,這是我最大的願望。
被國民故府軍所誘拐的台灣女性
戰後,除了傾家蕩產,被國民政府軍所拐騙而被迫參加國共內戰的一萬多名台灣兵之外,還有些是被國民政府的軍宮所誘拐而隨著軍隊的移動渡海到中國大陸的台灣女性。
終戰初期,進駐台灣的國民政府軍隊主要是占據台灣各地的學校或公家機關的空屋,因為這個關係,許多學校的女教員或機關的女性職員以及民家少女被誘拐、暴行恐嚇,乃至全家被滅門的事件層出不窮,這樣的殘暴行為在日治時代是非常少見的。可見台灣人對當年國民政府軍官兵的作為會感到氣憤是當然的事。
「這樣軍隊是祖國的軍隊嗎?」
「什麼叫同胞!比日本人還殘暴!」
「混蛋的傢伙!難怪日本人罵他們是清國奴啊!」
「要把女兒嫁給外省人,不如殺了餵豬!」
各地的台灣民眾的咒罵以及憎惡之聲不絕於耳。
終戰還不到一年,台灣人對「祖國」的愛情,從熱望變成希望,從希望變成失望,而更進一步的跌入絕望的深淵。終於在一年半後的1947年2月27日,在臺北市,因為「取締私煙」而成為隱藏在台灣人民心中悲憤的導火線,在第二天(2月28日)爆發了「抗暴事件」。
當然「228事件」發生的遠因,不只是國民政府軍對台灣女性的暴行以及取締私煙的問題而己,其他的政治、經濟、文化、軍律及對各種事物的價值觀等等問題都複雜的糾葛,終於發生了像火山爆發一樣的大事件是無可置疑的。
在終戰初期,進駐到台灣的國民政府軍的官士官兵誘拐了不少台灣女性,其主要原因:
a. 國民政府軍的官兵,以「戰勝者」的姿態君臨台灣,到處逞威。
b. 軍規軍律非常紊亂。
c. 「近水樓台」(因為駐屯場所上關係與女性接觸機會多)
d. 有些台灣人有潛在學習中國語的意識存在。
e. 被黃金戒子或手鍊誘惑。
1946~47年,派駐台灣的國民政府軍第六十二軍先到東北的錦州支援,而整編第七十師,則到山東省西部及徐州的支援於後。到大陸的台灣兵都以上海為第一個地。軍方明知道軍隊會移動到戰地,但這些國民政府軍的軍官卻故意隱瞞真相,把許多的台灣女性帶到中國大陸去。船雖然安全的到達了上海,但是這以後所遭遇到的「不幸」,這些台灣女性那裡會想像得到。
一旦到了中國大陸以後,台灣女性這才發現對方早已有了妻子,有的是無法適應那裡的生活和語言,因此被遺棄、被出賣的事倒是不勝枚舉。假如,沒有被遺棄或出賣,這些台灣女性被帶到「冰天雪地」的東北,也無法適應酷寒的環境。何況,部隊是去前線支援、作戰的,怎能帶著女人上軍!
所以,她們被留置在上海,雖然是被遺棄或像奴隸般地被賣掉了,但,這些人算是蠻「幸運」的。
這些女性幾乎都是不顧父母兄弟之反對,愛上外省人軍官或被誘拐而隨部隊去大陸後,美夢破碎,走投無路,又不敢返回台灣,為了生活,不得不走上賣春之路。
這些女性在上海市的花街掛起招牌,寫著「台灣女郎」而堂堂幹起拉客的生意,這種事情被派遣到上海的台灣海軍技術員兵們發現而引起騷動,一時成為茶餘飯後的話題。對一起生活在上海的台灣人來說,沒有比這個更羞辱的事情。
有一位被帶到山東省的臺北第三高女出身的女性,被對方的母親視為「海島番婆」身心受盡虐待,無法忍受而徘徊於青島海邊,想投海自殺而被我們救助的情景,我永遠難以忘記。
被吸鴉片煙的軍醫所欺騙的少女
滯留在雲南省的原國民政府軍野戰醫院當護士的黃月華,更遭遇到悽慘的命運。她是昭和4年(1929年)生於台灣宜蘭縣的一個貧苦家庭為長女,在終戰那年,連公學校還未能畢業的她,已是長得亭亭玉立的十七歲少女。
1945年10月,國民政府軍的部隊進駐到黃月華家的羅東鎮附近純樸小村莊,不知是否命運的捉弄,她竟然成為進駐村裡的國民政府軍官兵互相競爭追逐的對象。
這年年尾,貧窮加上母親突然病死,下面的妹妹便被送出人家養女。這麼一來失去母親及妹妹的悲傷,心裡甚為孤寂、無助。駐村部隊有一位軍醫胡上尉殷勤照顧,加上一個金戒指誘惑,終於贏得她的芳心。
到第二年夏天,她便不顧父兄的反對,和胡姓軍醫一起隨部隊的移動渡海到中國大陸。然而,「不幸」已經在等著她,他不但無法過著新婚夫婦的家庭生活,甚且每日過著危險、緊張的軍隊生活,尤其胡上尉在大陸已經有了妻子,而且後來才知道他是一個鴉片中毒者。
胡軍醫為了購買鴉片及嗎啡的錢,竟將她編入軍隊的護士班,領取她的薪水去買鴉片,有時毒癮發作時,就催促她去向人家借錢,不聽命時,便遭拳打腳踢,她只有忍氣吞聲變成沈默寡言。
不到一年,她已無法再忍受他的虐待,便和胡軍醫分手,後來輾轉許多野戰醫院,最後又和同野戰醫院的張中尉再婚,生下三男一女,成為四個子女的母親。
當我訪問她時,黃女士回想她的不幸遭遇,心痛地訴說她的心聲:
「1955年7月,在高呼『肅反運動』的呼聲中,我丈夫因出身原國民政府軍,立刻被貼上『歷史反革命』嫌疑者的標籤,每天晚上被公安叫去審問到深夜,對歷史問題(祖先歷代的經歷)加以審問,最後被判定牢役八年,外加勞改造十二年。」
生為台灣人的「原罪」
「我也是因為原籍是台灣而被送到煤礦去接受勞改,那時最大的孩子才八歲,最小的生下不到五個月,而且是遠離家鄉的台灣女性。我一個女人每天帶著幼小的四個子女去參加煤礦的重勞動作,因為營養失調,連餵孩子的乳水都擠不出來,甚至連養孩子的錢也沒有。」
「為了錢,我強忍著去加班工作,每天要到深夜才能回家,再做糊紙袋的工作。我比人家加倍的認真工作,但是我的薪資卻比別人少,一般的家庭都能獲得一日三餐的溫飽,而我們卻是一日二頓稀粥,要讓孩子吃飽都很困難。當時所配給的主食是雜糧,數量又少,我們只有經常去採野菜或果之類瓜來代替主食渡過飢餓,豬肉、魚味對我們來說是完全無緣的東西。」
「1966年2月,開始文化大革命,像我們這樣的人當然又成為鬥爭的對象。我丈夫的勞動薪資由每月29元被降低24元,而十五歲的長男,在學校被輕視,指為黑五類之子。下面的孩子們看了這種情形,深恐被人欺負,害怕得連學校都不敢去,每天哭泣不願意去上學,因此我的孩子們都沒有接受什麼文化(教育)。
「我不論如何努力去工作,我的薪資永遠比別人少,因此幾乎每天都在為生活而忙碌,有時候連買米的錢都沒有,我也沒有勇氣去向鄰居借錢,有時因為生病無法工作時,班長便立刻來調查,因為我是台灣人的關係,一直被監視著,因此一缺席,他們立刻就知道。難道是台灣人一生下來,就要背負這樣的『原罪』嗎?」
「我被前夫拐騙而來到中國大陸,我早就認命,只要當一位平凡的家庭主婦能夠渡過一生就好了,但是這四十年來,我在中國大陸所受到的苦難,是無法用筆墨所能形容的」。
已經是滿頭白髮的黃月華,一直擦著眼淚,把她長年藏在心中的「文化大革命」時所遭受到的痛苦向我訴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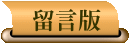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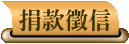


3 則留言:
活該 個人造業個人擔
"活該 個人造業個人擔!"
"人" 者 ? 人來人往..... "造業" 者 ! 無奈人間..... " 始作俑者 ",民族性也,尤以中國為甚,三國爾虞我詐,六國趕盡殺絕,一代殺一代.....
所謂 "活該 個人造業個人擔!",無非是樓上自己撒鹽,又是作孽、又是造業....
- - - < 騎高山、看牛相鬪 >。。。。
切記 : 人來人往、苦海人生,先生您何其幸福,此一時納涼喫茶、誰知道天雨時也該撐傘 !?
謝謝您的回覆,小弟會再蒐集相關資料對應,尋找先父魂歸何處,爾後有勞先生抽空回復,甚幸 !!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