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為千風──記台灣烈士許昭榮
◙涂建豐2008/8/11
私のお墓の前で 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
そこに私はいません 眠ってなんかいません
千の風に 千の風になって
あの大きな空を 吹き渡っています
秋には光になって 畑にふりそそぐ
冬はダイヤのように きらめく雪になる
朝は鳥になって あなたを目覚めさせる
夜は星になって あなたを見守る
私のお墓の前で 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
そこに私はいません 死んでなんかいません
千の風に 千の風になって
あの大きな空を 吹き渡っています
─────新井滿譯自英文詩
二○○八年六月七日中午,高雄縣鳳山基督長老教會,悠揚典雅、悲而不傷的日語歌聲緩緩傳來,奇美曼陀林樂團指揮蔡蕊微女高音,正演唱著日本音樂家新井滿從英文詩歌〈Thousand Wind〉翻譯而來的〈千の風になって〉(化為千風),近兩百位親友齊聚一堂,為台灣老兵許昭榮舉辦追思告別音樂會,此時此刻,我感覺到許昭榮正從天堂裡,安詳的看著教堂內的這一切。我心頭震了一下,五月底剛買到日本聲樂家秋川雅史單曲唱片〈千の風になって〉,這首曲子我每天總得聽上幾回,這優美的旋律經常在我腦海中浮現,就是要預示今日的情境嗎?
請不要佇立在我墳前哭泣,
我不在那裡,我沒有沉睡不醒,
化作千風,我已化身為千縷微風,
翱翔在無限寬廣的天空裡!
─────新井滿譯自英文、張桂娥中文翻譯
今年五月二十日晚上,我正在高雄光榮碼頭採訪新總統就職焰火表演,突然接到同業中央社王小姐來電說:「有個老兵在旗津自焚,名字叫許昭榮,好像是你朋友哦?」雖然當時天空下著毛毛雨,高雄市交響樂團正激昂演奏著柴可夫斯基的〈一八一二序曲〉,高雄港夜空閃爍著五彩繽紛、炫爛奪目的焰火,新總統正坐在真愛碼頭貴賓席微笑欣賞表演,渾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但我腦中卻似響起晴天霹靂:「我的朋友許昭榮真的自焚了嗎?到底為什麼要自焚?」
這個消息立即在新聞同業間傳開,部分政治敏感度較高的同業警覺到,「可能有政治因素」。我也相當確定,許先生雖已八十歲,但老當益壯,生命力旺盛,一定是有政治訴求,才會在這個特別的時間點,採取這麼激烈的手段。果然,資訊逐漸齊全──許昭榮遺書指責政府漠視四萬名台灣歷代戰歿英靈,至今未給予歷史定位,並抗議退輔制度不公,偏袒「老芋仔」,剝削「蕃薯囝」;議會亂武,司法亂彈,他甘願死守台灣唯一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直到催生國立的「台灣歷代戰歿英靈紀念碑」為止。
雖然夜已深,我還是打電話給當初介紹我認識許昭榮的前自立早報同事陳銘城,告訴他這件不幸。銘城已經知道了,在文化界以感情豐富著稱的他嗚咽地說:「我和總統府的朋友曾想辦法要讓許昭榮代表台灣老兵受勛,由陳水扁總統親自頒贈,也想辦法爭取經費蓋紀念公園,國防部不理,文建會沒辦法,就從內政部爭取到經費,但到現在還沒成功,都是我們沒將事情辦好,害死許桑!」
秋天,化身為陽光照射在田地間,
冬天,化身為白雪綻放鑽石光芒,
晨曦升起時,幻化為飛鳥輕聲喚醒你,
夜幕低垂時,幻化為星辰溫柔守護你。
─────新井滿譯自英文、張桂娥中文翻譯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二日,老同事陳銘城南下高雄縣鳥松鄉,要去某安養院採訪一位一生穿過「日軍、國軍、解放軍」三種軍服的台灣老兵-謝瑞生。銘城約我一起前往,「全國原國軍台籍老兵暨遺族協會」理事長許昭榮也同行,這是我首次與許先生見面。
謝瑞生是台南麻豆人,當時剛接掌警察大學校長的謝瑞智是他堂弟,不過,謝另位堂兄謝瑞仁則在白色恐怖時期遭國民黨槍斃。謝瑞生當年為了抗日,遠赴福建加入國軍,卻被共產黨新四軍俘虜,軟禁兩年後,被派任軍醫,並負責養馬。之後,他在皖南事件中被日軍俘虜,在安徽改當翻譯而倖存,後來攜械逃亡,再加入國軍。沒想到國共內戰,國民黨敗退台灣,謝瑞生卻一直留在中國,歷經勞改批鬥、擔任「消殺科長」負責殺蚊滅蠅‧‧‧。一九九一年經由謝瑞智協助,他才終於回到睽違半世紀的故鄉台灣。
許昭榮與謝瑞生是好友,也有著台灣人共同的命運,年輕時就被徵戰,到老還在為台灣人的尊嚴戰鬥。陳銘城為了策劃〈台灣人的戰爭展〉,透過許昭榮到處尋找有戰爭經驗的台灣人,事後集結成書出版《台灣兵影像故事》。許昭榮在訪談謝瑞生的文章中,感嘆「台灣子弟在外來統治者徵兵、募兵制度下,到底為誰而戰?為誰而死?為誰流離失所?」
我從這些心聲感慨,逐漸認識了許昭榮的背景。許先生從不是自怨自艾的無力者,而是即知即行的行動派,追尋台灣老兵的下落,成為他命定的人生功課。他自稱是「反骨老人的愚蠢事業(馬鹿仕事)」,即使到中國尋找戰友遺骨,被懷疑「台獨立場」動搖,他也不改其志。
許昭榮的軍旅生涯艱辛難言,但也激發他關切、投入民主運動,甚至因而兩度入獄,在綠島監獄待了十年。兩年多前發生紅衫軍事件,許昭榮痛罵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無情無義」、「背棄台獨理念」,因為當年他就是在美國聲援綠島獄友施明德,而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流亡海外長達八年之久。
許昭榮這段艱辛、豐富的人生閱歷,對身為新聞記者的我而言,當然是極佳的報導寫作題材,光是人物特寫,我就寫了兩次,分別介紹許先生推動「台籍老兵和平祈願公園」及興建「國共內戰時期投效國軍殞身台灣子弟兵紀念碑」,與出版《不為人知的戰後原日本軍、原國軍台籍老兵的血淚故事》日文專書,收錄一九九三年許昭榮參加日本產經新聞為日本皇太子成婚徵文比賽,批判日本政府漠視前台籍原日本軍權益,而獲得「敢鬥賞(最佳勇氣獎)」──日本文壇重量級人士阿川弘之拜讀後深有所感,遠從日本寫信給許昭榮,肯定許昭榮為歷史留下珍貴的記錄。
許昭榮的一生,無時不在爭取恢復台灣人的尊嚴。記得有一次與許昭榮談話,我問他最近忙什麼,他說「沒忙什麼,吃飽就找國民黨算帳而已!」當時,他正因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獲得國民政府賠償近四百多萬元,政治平反後,他馬上又為當年他遭到判刑後,國民政府馬上將他的家人從海軍眷舍掃地出門,房屋充公,要求國防部還給他一個公道。
每次在政治或社會運動場合與許先生不期而遇,我總是先用日文向精神矍鑠的他問好:「お元気ですか?」許先生也中氣十足地說:「元気!元気!」我與許先生最後一次見面是在今年四月二日,紅厝瓦餐廳的老闆劉明松因為謝長廷選輸總統,於是實現選前承諾,跳愛河游泳來回對岸,許昭榮出席了劉明松的行前記者會,他與劉明松還一起豎起拇指合照。那時的許先生一派心平氣和,絲毫沒有火氣,我來去匆忙,打過例行的招呼後,就趕往愛河採訪,許先生也不多話,微笑而已。
許昭榮就是這樣豁達,他喜歡與年輕人在一起,卻從沒端出「好漢當年勇」的架子;出版新書,一定馬上四處分送好友,請大家參考看看;回屏東枋寮老家時,總會記得提一袋當地土產洋蔥,給高雄的朋友當伴手禮。因為都喜歡日本料理,許先生就約我到享譽港都的「惠美壽亭」,傳說中頗有威嚴的老闆娘,見到許老先生卻是熱誠相待,日本籍的廚師老闆也親自出來招呼,許先生告訴我:「老闆可是建國黨極少數的外籍黨員呢!」
當時,我非常著迷日本NHK電視拍攝的大河劇,有一陣子正在播放〈秀吉〉,我手頭上剛好有一本NHK出版的〈秀吉〉專輯,我對茶道大師千利休為何被秀吉賜死的「歷史之謎」相當有興趣,就請許先生幫我將書裡面兩頁關於千利休的文章翻譯出來。許先生不僅爽快答應,而且才兩、三天就翻譯好了,和他自己寫書一樣,是用電腦日語輸入來寫出漢文,並以雷射印表機工整的列印出來。最近我整理資料時,這篇久違的翻譯竟然又出現眼前,讓我深信,這是許先生留給我的紀念。
我再次重讀譯文:「利休曾是秀吉的同志,秀吉在取得天下後,利休感受到夾在權力之間的一種虛無感,切腹是他最大的自我主張!」從未躋身政治核心的許先生,也曾未有虛無感,但在不義體制下,選擇自焚,「寧願燒盡,不願銹壞」,難道也是種最大的自我主張嗎?
又過了一陣子,我整理積存許久的電子信件,赫然發現,政治大學新聞系林元輝教授去年十二月間傳給我,主題為〈關不住的歌聲〉的電子信中,連結到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於二○○六年中元節(也是父親節前夕),在高雄二二八事件中死傷最慘重的愛河畔所舉辦的「普渡台灣魂音樂祭—為台灣父兄獻唱」活動時,台灣友人馬修‧連恩(Matthew Lien)演唱〈Danny Boy〉(丹尼男孩)的短片。演唱中打出字幕──黃守禮教授在清鄉白色恐怖的一九五○年代,是台北工業學校的學生,莫名被捕,關在保安司令部。愛唱歌的黃守禮借著歌聲為難友打氣,隔壁囚房的台大學生于凱,是一位隻身從山東來台的流亡學生,在即將被槍決前,他懇求黃守禮為他唱〈Danny Boy〉,想到遠在中國老家的母親,不知兒子將在台灣被槍決,猶苦苦守候家門‧‧‧。
〈Danny Boy〉原來是愛爾蘭民謠,描述一位母親想念被徵召出征的兒子「丹尼」,既擔心兒子回不了家,又擔心兒子回家時,自己已經不在人世,萬般不捨的心情,感動無數人心,不僅與〈夏日最後玫瑰〉、〈強尼當兵去〉同為愛爾蘭最負盛名的三首民謠,更已成為「反戰歌曲」經典作品。
許昭榮追思會中,許的外孫女洪翠嶷,除以長笛演奏了台灣人耳熟能詳的〈補破網〉、〈綠島小夜曲〉外,也演奏〈Danny Boy〉。司禮人林景熙傳道師很驚訝地說,這是母親懷念兒子的反戰歌曲,為何孫女要用來紀念阿公?翠嶷說:「回想與阿公的相處,腦中自然浮現這個旋律!」然而,我的感受卻是非常貼切,因為這個懷念兒子的母親就是「台灣」,這個一輩子為母親努力打拚的兒子就是「許昭榮」,翠嶷只是順著上天的旨意,以樂音撫慰阿公,也撫慰在場的所有許昭榮的親友。
請不要佇立在我墳前哭泣,
我不在那裡,我沒有離開人間,
化為千風,我已化身為千縷微風,
翱翔在無限寬廣的天空裡!
─────新井滿譯自英文、張桂娥中文翻譯
許昭榮確實「化為千風」,他不僅守護著台灣唯一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還留給親友無限懷念。不幸的噩耗傳來之後,被我設定作手機來電鈴聲的〈化為千風〉在追思告別音樂會中重新迴盪旋律;然後我發現了許先生留給我的日文翻譯資料;接著整理電子郵件時發現林元輝教授傳給我的電子信,竟然是〈Danny Boy〉‧‧‧。種種線索都暗示著,許先生並未遠離,他一直在我們身邊。
參加六月七日追思會時,我遇到許多久違的好友:從台北下來的自立報系同事陳銘城、彭琳淞(最先為許昭榮撰寫長篇人物傳記者)、攝影家潘小俠、侯聰慧,在高雄的台灣歌謠創作家鄭智仁、王明哲、書法家陳世憲,與第一時間趕到旗津自焚現場後,即持續協助處理後事的黃旭初,我突然發現,原來許先生是我們的共同交集!
從未公開落淚的我,有一天晚上竟然在夢中因許先生的逝去流淚不已,醒來之後,卻逐漸清醒、堅定,許先生的英靈,真的還是在照顧著大家。
這是以往我不曾有過的觸動,從前聽到「某某人雖不在人間,但精神與我們同在」之類的說法,其實都沒有太多感受,直到最近這兩年接觸許多靈學的概念,才逐漸認同:每個人到這個世界,都是帶著「功課」而來的。如果是這樣,許先生的「功課」,不也是台灣人共同的「功課」嗎?要建立一個正常健全、公平正義的獨立國家,讓國民都享有民主尊嚴,那需要多大的願力!而許先生的自焚,在台灣這複雜的「功課」中又具有何種意義呢?
為了解答內心疑惑,我透過朋友詢問知名的通靈人士「伶姬」。她果然表示,許先生面臨的政治格局,正是他這輩子要面對的「功課」,但自殺永遠不是好辦法,下輩子,他還是要面對相同的政治難題,就看他會不會有更好的方法去解決,那才是真正完成「功課」。
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的許昭榮,到時將要面對什麼樣莫測的政治情勢呢?我們這一代要如何打開局勢、共創台灣未來,迎接下一世的許昭榮呢?許先生留下來的「功課」,令我低迴不已‧‧‧。
skip to main |
skip to sidebar
協會
高雄市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二路701號
(風車公園旁)
TEL:(07)571-9973
FAX:(07)571-9973
信箱:tw.war.what@gmail.com
------------------------------------------
◆戰爭與紀念和平公園網站
◆《台籍老兵相關系列活動》
(風車公園旁)
TEL:(07)571-9973
FAX:(07)571-9973
信箱:tw.war.what@gmail.com
------------------------------------------
◆戰爭與紀念和平公園網站
◆《台籍老兵相關系列活動》
最新文章
序
化為千風
動盪時代的無奈─台籍老兵血淚故事
追思與懷念
附錄
英文區
日文區
懷念許昭榮及相關連結
▲觀念平台-台籍老兵的苦戀
▲化為千風~投稿台灣文學評論
【涂建豐】
▲林忠雄
▲許昭榮先生追思告別會
▲台籍老兵許昭榮自焚身亡
▲許昭榮,美麗的仗已打過了
▲一位台籍老兵的死--許昭榮先生的
死諫
▲守護台籍兵 許昭榮自焚明志
▲懷念許昭榮先生
▲化作千風:寫給許昭榮,與他的遺
願
▲一位老前輩
▲台灣老兵許昭榮高雄旗津自焚身亡
▲老兵與老牛-紀念許昭榮先生
▲台籍老兵許昭榮給我的啟示
▲哀許昭榮自焚
▲由台籍老兵許昭榮自焚事件-看中
華民國國民黨的治台史
▲正港台灣魂 許昭榮的大苦行
▲追思許昭榮老先生
▲悼台籍老兵許昭榮先生
▲台籍老兵許昭榮520在旗津自焚
▲有誰願意聽他們說
▲一首不平凡的悲歌-悼台籍老兵許
昭榮叔叔自焚身亡
▲「人‧島‧主體性」之旅-許昭榮
▲悼念許昭榮兄~一個真台灣正港台
灣人
▲敬悼死不瞑目的「台灣老兵」
▲前國軍台灣老兵的血痊G事
▲悼念!許昭榮爺爺
▲追思台籍老兵許昭榮-學界編紀念
專輯
▲越南最後一個台灣兵
▲化為千風~投稿台灣文學評論
【涂建豐】
▲林忠雄
▲許昭榮先生追思告別會
▲台籍老兵許昭榮自焚身亡
▲許昭榮,美麗的仗已打過了
▲一位台籍老兵的死--許昭榮先生的
死諫
▲守護台籍兵 許昭榮自焚明志
▲懷念許昭榮先生
▲化作千風:寫給許昭榮,與他的遺
願
▲一位老前輩
▲台灣老兵許昭榮高雄旗津自焚身亡
▲老兵與老牛-紀念許昭榮先生
▲台籍老兵許昭榮給我的啟示
▲哀許昭榮自焚
▲由台籍老兵許昭榮自焚事件-看中
華民國國民黨的治台史
▲正港台灣魂 許昭榮的大苦行
▲追思許昭榮老先生
▲悼台籍老兵許昭榮先生
▲台籍老兵許昭榮520在旗津自焚
▲有誰願意聽他們說
▲一首不平凡的悲歌-悼台籍老兵許
昭榮叔叔自焚身亡
▲「人‧島‧主體性」之旅-許昭榮
▲悼念許昭榮兄~一個真台灣正港台
灣人
▲敬悼死不瞑目的「台灣老兵」
▲前國軍台灣老兵的血痊G事
▲悼念!許昭榮爺爺
▲追思台籍老兵許昭榮-學界編紀念
專輯
▲越南最後一個台灣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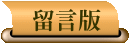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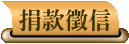


1 則留言:
我是許照榮烈士生涯的最後二年能得到朝日相處的人(許先生的壯烈犧性讓我無法說出幸運這兩個字)、他是在我的人生中唯一這麼靠近的心目中偉人、到現在我無法相信他己不在人世、我一想到他、我會流淚我在哭。
在我的認識中、許先生是幾近完美的人、健康、意志堅定、待人親切和藹、熱心、完全沒有私心、有時急躁、固執卻是來自這些特性、我一直稱他「先生」--是日語中受尊敬的老師。他引導我認識廣大的有愛心的台灣及日本的同好、林牧師、江教授、王明哲、陳明城、薛宏甫、、、諸先生、還有想見面的黃旭初先生、、、等。許先生連接了我們、感激不盡。
我已經長住日本、無法參與在台灣的每一紀念許先生的行事、看到台灣各位許先生的朋友努力在保存及完成許先生的遺願感激不盡、許先生的人格才可能得到這樣的殊榮、但我還是會為許先生做到我尊敬他懷念他所應該做的事。
感謝各位朋友以外、我還要向在背後支持許先生的余美智 夫人致敬。
有許多像許先生這樣的人、台灣一定會獨立、建立一個有愛心、有公義的國家。
在日 周振英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