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意外的災禍中一轉,我終於名副其實的獲得了「自由」之身。
接受了加拿大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後,我想起在當時的台灣是絕對無法辦到的,或者說是不可以辦「尋找滯留中國大陸的戰友及遺骨」之事。因對象不只是日本政府時代的戰友,也包括戰後被國民政府軍隊所欺騙或拉丁,再送到中國大陸前線去作戰而失蹤的國民政府時代的戰友。我當時也被強迫到中國大陸的青島,所幸我被配屬到「青島海軍軍官學校接艦班」,後來被配到司令艦,才能隨著國民政府的撤退,平安回到台灣。
▼許昭榮在中國尋得失蹤的同鄉同學王喜森(左)(屏東縣水底寮人)
.jpg) 在爾後的40年間,我的心中一直牽掛著1949年,因「太湖」護衛艦的誤射事件,被我遺棄在渤海長山島上的戰友林淵嵩君的遺骨,以及和我一樣被迫到中國大陸的同鄉:王喜森及王添興二人失聯,這兩件事,一直到現在還耿耿於懷。
在爾後的40年間,我的心中一直牽掛著1949年,因「太湖」護衛艦的誤射事件,被我遺棄在渤海長山島上的戰友林淵嵩君的遺骨,以及和我一樣被迫到中國大陸的同鄉:王喜森及王添興二人失聯,這兩件事,一直到現在還耿耿於懷。如前途,在1986年,台灣人民還處於「戒嚴令」及「白色恐怖」的恐懼下,不要說是尋找「殘留在中國的原國民政府軍台籍老兵」,連他們的家族要向國防部探問自己兒子或是兄弟到底在那裡的事都不可能的時代。
是居住加拿大以後,這些恐懼、憂慮完全不存在了。受了這個恩澤,我便能夠自由自在的向中國的報社寫信,請他們協助尋找林淵嵩君的遺骨及兩位王先生,但是經過幾個月連一點回音都沒有,我已經對被稱為「鐵幕」的中國共產黨的「麻木不仁」感到失望了。但是我對探尋戰友的信念一點也沒動搖。
有一天晚上,我睡不著的一直望著天花板想東想西的,突然腦裡閃過一道思維。第二天,就造訪多倫多大學的圖書館,在那裡的東亞館,我發現了北京的「全國台灣同鄉聯誼會」(簡稱全國台聯會)的會刊《台聲》雜誌,以及舊日本海軍的「新竹航空隊戰友會」的存在,我好像在水中抓到水草一樣,馬上給《台聲》雜誌社寄出請求協助「尋人尋屍」的信函。
經過三個禮拜後,《台聲》的閻崑記者給我回信,要問我的中文名字及林君的詳細資料,我激動得幾乎要跳起來。
在1987年的年尾,由於閻先生的熱心及人道主義精神的所賜,終於查出林君的屍骸埋葬在島上的「亂葬岡」(夭折的小孩、或異鄉人、家畜等埋葬的地方)、而王添興君早在1959年,因罹患肺結核病在山東省濟南市第三醫院療養中死亡,王喜森君仍健在,住在上海市。我的「尋人、尋屍」的消息刊登在北京的《台聲》月刊後,散居在中國大陸各地的原國民政府軍技術員兵(海軍)接二連三的感謝及求援的信件,經由閻先生之手送到多倫多我的住處。特別要提起的是,做夢也沒想到我的「尋人、尋屍」活動,竟引起多數滯留在中國大陸的原國民政府軍第七十師及第六十二軍(陸軍)的台籍老兵的共鳴。
但是很遺憾的是,當時我連去中國大陸的「難民護照」也沒有。
滯留中國的台灣老兵救援工作
1988年4月17日,根據北京的閻先生所寄來殘留中國的原國民政府軍台籍老兵的調查資料,我開始為他們發出救援工作的聲音。最先呼應我的是派駐在紐約的《中國時報週刊》特派員周昌龍先生。他立刻打電話到多倫多採訪我。並於第166期的《時報週刊》上,用大標題的〈殘留在中國的十八位台灣老兵〉獨家,報導滯留在中國的原國民政府軍台籍技術員兵的悲情,呼籲國民政府做人道的救援。

▲這是國府軍陣亡將士的亂葬岡!每個土塚下面,像堆埋感染「口蹄疫」的死豬潦草堆裡埋著幾
十具國府軍陣亡將士之屍體。經過半世紀的歲月,依然被遺棄在東北、華北、華東地區的古戰
場,無人無問!其中,不知埋葬多少「台灣無名戰士的冤魂」,無法回歸故土!
以此為開端,第二天臺北《中時晚報》即以〈台灣老兵,三聲無奈〉標題轉載《中國時報週刊》的獨家報導,就這樣「滯留中國的原國民政府軍的台籍老兵問題」開始在國內被提起,但是台灣一般民眾卻誤認為「滯留在中國的原日本軍人軍屬台灣兵」。
1988年11月5日,我再度以求援的信函,用〈告知海外的仁人君子,請援助40年間被遺棄在中國的原國民政府軍的台籍老兵,完成他們自由歸鄉探親的悲願〉為題目的呼籲書,寄給紐約的《台灣公論報》及洛杉磯的《太平洋時報》。
▼與田邊芳昭社長(左)一起踏上中國尋人
.jpg) 為了援助滯留大陸台籍老兵的歸鄉旅費,我利用母親節的晚會進行募捐,但是總數加起來折合美金只有三千元而己,而且被從台灣來多倫多訪問的民進黨「國大代表」洪奇昌先生澆了冷水,尤其是台灣意識濃厚的多倫多台灣同鄉會的理事會決議:「用台灣同鄉會名義對北京寄送金錢是不可能的」。連我苦心慘澹所募集的僅僅3千美金支票也被退回了。但很幸運的,全美台灣人權協會的黃根深理事長及莊承業事務局長,很熱心的支援了我的工作。
為了援助滯留大陸台籍老兵的歸鄉旅費,我利用母親節的晚會進行募捐,但是總數加起來折合美金只有三千元而己,而且被從台灣來多倫多訪問的民進黨「國大代表」洪奇昌先生澆了冷水,尤其是台灣意識濃厚的多倫多台灣同鄉會的理事會決議:「用台灣同鄉會名義對北京寄送金錢是不可能的」。連我苦心慘澹所募集的僅僅3千美金支票也被退回了。但很幸運的,全美台灣人權協會的黃根深理事長及莊承業事務局長,很熱心的支援了我的工作。這時候,台灣國內的媒體也開始正面的報導「滯留中國的原國民政府軍台籍老兵」的境遇及苦痛,立法委員也開始批判國民政府的不公平政策,某個新聞的社論也上提出「對滯留中國的台灣兵施行返鄉限制是不人道的」強烈批評,但是那這些國民政府的高官及國防部幕僚卻一點也不為所動、一點也不知恥,連動都不動的毫無作為。
從加拿大出發探掘戰友的遺骨
1989年2月加拿大政府發給我「難民護照」。我馬上打電話給岡山市的「遠藤青汁之友會」的田邊芳昭社長告訴他這個喜訊,於是互相約定在同年2月28日(台灣228事件42週年紀念日)在大阪機場會合後,一起到北京。但是,萬萬想不到駐多倫多的日本國領事館,卻把我的日本「入國簽證」退回,我只好抱著對日本政府、滿胸悲情的心情,臨時變更行程從加拿大的多倫多直飛北京。從飛行在太平洋上空的飛機視窗望浩瀚的水面,我一回想日本外務省的冷酷無情,直覺得日本和台灣是越走越遠了。
首次和來北京機場迎接我的閻記者見面。第一眼瞥見他是一位30歲左右、中等身材外貌上相當有教養的青年,第二天,我們去迎接從大阪飛來的田邊社長,然後馬上飛往煙台,從煙台登上大型渡輪到長山南島。
長山島現在升格為「長島縣」,是屬於山東省的行政區管轄,位於遼東半島及朝鮮半島間的黃海上的長山群島的行政、經濟、軍事、交通重鎮。群島是由八個主要島嶼所形成,近年來,在這個海域,因為養殖幹貝(小型)及大黑蝦(對蝦)而迅速地發展;照島民的說法,在這裡的幹貝生產量占全中國總生產量的六成。交通很發達,從煙台每天有好幾班大型渡輪在航行。
總之,長山島的經濟和四十年前有天壤之別的發展,到處是五層樓建築的漁民公寓,道路都是水泥鋪設,在街道的兩側用水泥造的圓形種花盒(植木缽),像儀仗隊一樣成列排著,種著牡丹或花等和一些不知名灌木,像在歡迎我們到來一樣的很醒目。
因為閻先生的努力,不但《台聲》雜誌社、山東省及煙台市台灣同鄉會、長島縣政府及北京中央電視台也都派員陪同,支援我「探掘屍骨」的工作。但最遺憾的是因田邊芳昭社長是日本人的關係,而被禁止進入長山島的要塞地區,只好留在煙台市內等候我們。
在四十年前的1949年,林君因為護衛艦「太湖號」的訓練不足,而發生艦砲誤射事件「枉死」,但艦隊司令官黎玉璽少將及艦長張仁耀上校為了湮滅真相,而向國防部偽報為「戰亡」,想把遺骸加予「海葬」。不滿艦長之作為,自告奮勇接受遺體的善後處理工作,想要把林君的遺體運回台灣,並且可追究事故的責任,為枉死的林君的無辜討個公道,我帶領四位士兵,把林君的遺體用擔架送到長山島上,計畫暫時埋葬在海灘上,待戰事結束後,再掘起來運至定海空運台灣。
但是那天晚上,大家在為林君做守靈時的深夜,長山島被中共的軍隊包圍,受到襲擊,雖然盡力抵抗,最後還是失守。駐軍有的投共有的撤退。因此不得不把林君的遺體放置在附近的小寺廟,突破中共軍的包圍,經過6小時在渤海上漂流,終於被通過的海防艦「海明」救起。
▼太湖艦
.jpg) 為了當年來不及埋葬遺體的事,我才會在四十年後從遙遠的多倫多來到這裡探掘。這可能就是我長年累月留在胸中的林君的遺影,在冥冥之中要我來完成這件事,連我自己在回顧前後的軌跡時,都有這種微妙的感覺。
為了當年來不及埋葬遺體的事,我才會在四十年後從遙遠的多倫多來到這裡探掘。這可能就是我長年累月留在胸中的林君的遺影,在冥冥之中要我來完成這件事,連我自己在回顧前後的軌跡時,都有這種微妙的感覺。經由島上長老們的指點,「這裡就是埋葬你的戰友遺體的亂葬崗」。當他們指著水泥地的庭院時,我真的發楞了,這不可能是以前的「亂葬崗」吧。
「是真的,你看那棵樹就是標記,我家就建在樹的右邊,絕對沒有錯。」當那位在長島縣政府擔任副書記的潘忠興先生這樣說時,其他的長老們也同聲附和。
我只好按照大家的指示,雇用島上唯一的一輛大型挖土機,開始挖掘礦物局的水泥地庭院,隆隆不斷的機器吼聲及挖掘砂粒的刺耳堅銳聲中,現場的人都屏息凝聲,一直在注目著白骨的出現,但是並不如所望。
▼挖到棺材和幾塊碎骨後作者一面上香、獻菓、點燃冥紙,一面流
淚向林淵嵩致歉,並祝禱冥福。
.jpg) 換了位置,並且把範圍擴大,繼續挖了將近2小時,終於發現了幾片小小的白骨碎片及二片像棺材底板的木板,從還沒有完全腐爛的木板心中可以嗅到檜木的味道,那在亂葬崗不可能見到的「壽棺」(為自己的死後所預先準備的棺材)的味道,絕不會錯。那是當年島上一位慈悲的村長,看我們要把士兵的屍體直接埋入土中,覺得可憐而不惜把自己的「壽棺」捐出來的深情「珍貴的禮物」。真是感謝,沒有錯,應該謝天謝地。這就是當年大家一邊拭淚共同搬運來的棺材,我這樣下定判斷。
換了位置,並且把範圍擴大,繼續挖了將近2小時,終於發現了幾片小小的白骨碎片及二片像棺材底板的木板,從還沒有完全腐爛的木板心中可以嗅到檜木的味道,那在亂葬崗不可能見到的「壽棺」(為自己的死後所預先準備的棺材)的味道,絕不會錯。那是當年島上一位慈悲的村長,看我們要把士兵的屍體直接埋入土中,覺得可憐而不惜把自己的「壽棺」捐出來的深情「珍貴的禮物」。真是感謝,沒有錯,應該謝天謝地。這就是當年大家一邊拭淚共同搬運來的棺材,我這樣下定判斷。泣求戰友在天之靈的諒解
經過文化大革命時的「鞭屍」;墓地的整頓;而後的碼頭建設,以至現在興建的礦物局職員宿舍及庭院。這40年歲月間的變化是如此的巨大,而在這情況下,還能找出象徵性的遺骨及棺材的片段,只這些,我已能對這次來這裡的目的感到欣慰。
總之,我已盡力而為,我為林君在天之靈獻上一把檀香。
「林君,我來看你了,從遙遠的加拿大飛來。你還記得嗎?我是許昭榮啊,你還對我有怨恨嗎?40年之長時間,把你丟在這裡,真是對不起,你一定很辛酸吧!我也是一樣。我從未想到要把你放在這裡。所以,40年來,我為了你的事一直無法放下心來。」
當年,我不顧艦隊司令官及艦長的命令,拒絕海軍認為是傳統禮節的海葬,一心一意想把你的遺體運回台灣。讓你父母兄弟能看到你悲慘死亡的狀態,以便公開追究事故的責任,不僅要求兵員的訓練及管理的加強,同時為你的無辜之死討回公道,因此,把你的遺體搬到陸上,但是實在不幸,在深夜時,中共的八路軍乘著「太湖」、「太沼」艘姊妹艦出海巡弋葫蘆島及營口海域的空檔登陸長山島,展開了激烈的戰鬥,在等不到援軍的情況下,黑山島要塞的守備軍叛變倒向敵軍,到了清晨,整個長山島已被敵軍包圍。手無寸鐵的我們,看到敵軍逼到眼前時,只好退到海邊,在跳海、被殺,或被俘的緊急情況下,只好把你的遺體放置在寺廟裡,急忙登上被廢棄在岸邊的小舢板,在敵人的機關槍掃射下,用帽子和兩手拚命的劃水,經過六小時的漂流後,很幸運的被友軍的海防艦「海明號」救起,才能活到今日,甚至來到這裡……」
「淵嵩啊!請原諒我。這可能就是我們的命運,你在這島上忍受了40年嚴厲的風雪之寒,這樣的孤獨和苦難,我無限的同情,但是現在和40年前已不一樣?長山島已經不輸給台灣的漁村,並接受經濟發展的恩惠,也許,您已經轉世在這島上某個富裕的家庭……」
「今天,我從遙遠的加拿大帶來你最喜歡的美國巧克力和夏威夷的瑪卡蓬米亞豆,特別是你所懷念的故鄉台灣的鳳梨酥。不要客氣,儘量享受吧!」
「淵嵩,今日,可能就是我們兩個真正告別的最後時刻。我可能不能再來看您啦!我已兩頰滿淚,兩手合掌向您泣求,向您致歉。」
我雖然沒有抬頭,但我意識到圍觀人士也有人在陪我流著眼淚。
「林君,請您安息吧。我由衷祝禱您的冥褔。」我一邊燒冥紙一邊說。
獻上最後的默禱之後,我鄭重地把骨片和兩塊木板用報紙包上帶回多倫多。
挖土機把土地再整平後,我把挖土機的工資及修舖水泥的費用交給礦物局的值班人員,準備離開長山島時,煙台市台灣同鄉會副會長簡義春先生才告訴我:這裡有一位台灣老兵!
「既然知道,非去探望一下不可」我說。就這樣,被引導去拜訪的是屏東縣潮州出身的潘天元先生家。
那是一間用土塊砌牆圍起來的平屋,也是山東鄉村傳統的一般農家住宅。屋頂蓋的是瓦片,看起來已經耐過相當長的霜雪歲月;和鄰近新建的鋼筋水泥五層樓房相比,一眼即可看出貧富之差距。
圍牆的大門,經過長年的風吹雨打,日曬雪凍,已經褪去原來的顏色,好像舊棺材蓋子,令人感到多麼落寞、委屈。
簡副會長拉起生銹的門環叩了幾下。接著大門嘎的一響,一位中年男性探頭出來,讓我們進入屋內就座。我環視一下客廳,牆壁的塗裝已經剝落,處處可看到露出的土塊。牆壁上掛著一幀老婦人的遺像。我判斷潘先生的太太已經往生。
不久,潘先生臉上顯露驚喜的表情,從房間裡出來。他身材高大,看起來好像超過75歲。他操著濃厚的山東口音,向我們打招呼之後,請我們進去他的房間。
他說,很久沒有講台灣話,所以差不多都忘了。但還能說一些日本話。於是,我們就用日語交談。
▼長山群島上唯一的台灣老兵潘天元(左,屏東潮洲人),他當過日本軍夫
、國府軍醫務兵、中共人民解放軍戰士;參加過二次大戰、國共內戰、
抗美援朝戰爭。他證實國府七十師及六十二軍曾經在台「募兵」的秘史。
.jpg) 潘先生是大正10年(1921年)出生於台灣屏東縣潮州,而在台東卑南長大,太平洋戰爭中被徵用為軍屬,在南方戰線經過轉戰苦鬥中迎接終戰,但在復員回到台灣後,因為失業而煩惱。某天,因為看到「兵員募集,島內勤務,月薪二千免費教導北京話,退役後,可轉任公職人員」的廣告,因此去參加應徵而造成今日的結果,現在真是無限感概。
潘先生是大正10年(1921年)出生於台灣屏東縣潮州,而在台東卑南長大,太平洋戰爭中被徵用為軍屬,在南方戰線經過轉戰苦鬥中迎接終戰,但在復員回到台灣後,因為失業而煩惱。某天,因為看到「兵員募集,島內勤務,月薪二千免費教導北京話,退役後,可轉任公職人員」的廣告,因此去參加應徵而造成今日的結果,現在真是無限感概。他從日本兵,國民政府軍、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接連地換了政府被驅上前線去打仗,最後從朝鮮戰爭的前線身份,回到中國大陸,接著又被配置在長山島當碼頭的守衛而和島上的女性結婚,生了兒子、也當了祖父,就這樣長山島變成他的第二故鄉,也就死了心把這裡當做最後的葬身之地。
「還想回台灣嗎?」我問他。
「在死之前,很想回台灣看看。」他很寂寞地說著。
「中國大陸還有多少的台灣老兵呢?」
「除了戰死及餓死以外,全部成為俘虜,但都分散在各地,到底有多少人,不太清楚,可能有二、三千人左右吧!」
「有互相連絡嗎?」
「哪有可能?」
「為什麼?」
「大家互相不知道住處,就算是知道也無法連絡啊!」潘先生一直搖頭。
「您太太呢?」
「前年過世了。」
在談話中,潘先生漸漸紅了眼眶。
「來!拍張照片吧!」我把話打斷。
和潘先生祖孫三代一起拍了照片後,我們就互相告別了。
「潘先生,要保重哦!下次希望能在高雄或是在潮州見面啊!再見!」我說著和潘先生緊握住了手,鼓勵他。
走過舖著砂石的庭院小徑,我覺得足步比來時沈重。出了大門,我轉過頭,想再一次向潘先生說一句:「保重、再見」時,看到潘先生不斷地用穿著的藍色列寧裝上衣的長袖拭擦眼淚。看到這種的情景,我的眼眶也禁不住跟著灼熱起來,喉嚨竟像什麼堵住似的說不出話。我無言地向他揮揮手,很難過的快步離開傷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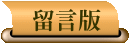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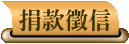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